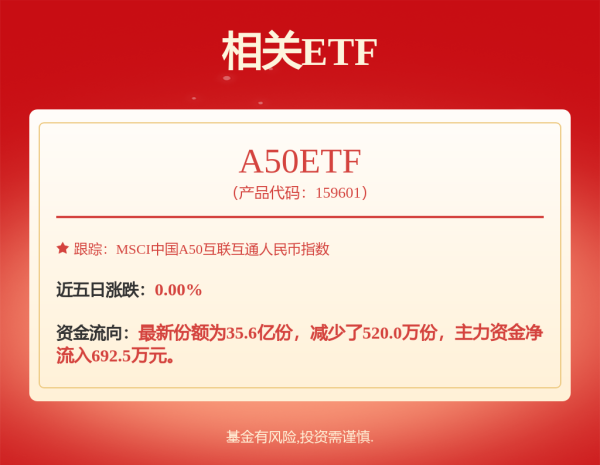陈顼,南陈的第三位皇帝,生于动荡年代,长于异国权势之下,登基过程波诡云谲,身后又以“高产皇帝”闻名。他原本并非皇位的直接继承人,却最终坐上皇位,并在南陈短暂的历史中留下了重要一笔。可令人疑惑的是,这位在兄长面前誓言“永不夺嫡”的皇弟,为何最终却废掉年幼的侄儿优股平台,自立为帝?
陈顼的出身在当时属于“次支宗室”。他的父亲陈道谭是南陈开国皇帝陈霸先的长兄,早逝于乱世中。因而在家族中,陈顼及其兄陈蒨由叔父陈霸先抚养长大。青年时期的陈顼命运多舛,24岁时,因随前朝太子萧方智驻守江陵,城破后被西魏俘虏,流落长安,成了名副其实的人质。
在他流亡的八年间,中国南北政局剧变。南梁灭亡,陈霸先于建康称帝,建立南陈;西魏则被宇文家族所取代,改国号为北周。陈顼的“主人”也从西魏变成了北周,身份更趋尴尬——既是前朝皇族,又是敌国俘虏,名为人质,实则无所依凭。
展开剩余78%公元559年,陈霸先驾崩,因亲生儿子陈昌尚在北方为人质,皇位由其侄陈蒨继承,是为陈文帝。此时,陈顼尚滞留北周,兄长陈蒨虽身登大位,却无法与弟弟团聚。
北周随后释放了太子陈昌。彼时局势微妙,北周此举显然是意图激化南陈的皇位继承矛盾:太子回国,自然要索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皇位。陈昌对此毫不掩饰,他一路高调返回南陈,途中多次致信建康,命陈文帝准备礼仪迎接禅让。此举在朝野间引发震动,许多大臣惶惑不安。
面对堂弟的“回归”,陈文帝内心不无动摇。他虽然已为皇帝,但毕竟名义上只是“暂摄国政”,而陈昌则是皇太子、皇长子,理应继承皇位。正当局势胶着之际,陈文帝的心腹将领侯安都主动出手,带兵迎接陈昌时,制造“落水意外”,将其沉于江底,事后对外宣称其“不慎溺亡”。
陈昌死后优股平台,陈文帝亲自为其举丧,悲声哀哀,一切似乎皆依礼制。但从此刻起,皇权旁落的危机便暂时解除了。
陈顼仍在北周囚禁,直到公元562年,陈文帝遣使与北周议和,割地求和,北周遂将陈顼放归南陈。此时陈顼已32岁,在北方度过了整整八年的“囚徒岁月”。归国后,他被哥哥授以重任:中书监、都督扬南徐等五州军事、扬州刺史、骠骑将军等一系列重要职务一并加身,可谓集军政大权于一身。
原因不难理解,南陈的皇族子嗣极为稀少。陈霸先一系子孙几乎全部战死或早亡,至此只余陈文帝与陈顼两兄弟。太子陈伯宗年幼不堪大任,陈顼便成为理所当然的辅政核心。
正因如此,兄弟二人都在拼命“增产”。据史书记载,陈文帝共育十三子,而陈顼则更胜一筹,前后共育四十二子,世称“最能生的皇帝”。这些子嗣多数得以善终,在隋朝仍保官职,不乏太守、刺史之属,成为南朝亡国皇族中结局较为优渥的一支。
然而,政治从不只是家族温情的延续。
公元566年,陈文帝重病,临终前将弟弟召至榻前,说出了一番令人玩味的话。他提到年幼太子,表达了效法古人“禅让于贤弟”的意图。陈顼闻言跪地哀泣,坚决辞让,按《陈书》记载:“顼拜伏泣涕,固辞不受。”
这一幕有些像表忠,也像试探。事实上,陈文帝并未当即传位,而是召集重臣商议。被召者有尚书仆射到仲举、五兵尚书孔奂、吏部尚书袁枢、中书舍人刘师知,皆为政坛骨干。其中,孔奂还是孔子的第三十一代孙,可谓名门之后。
朝臣们纷纷表示,皇帝之弟当辅佐幼主,必不生异心,言辞恳切。陈文帝闻言,似乎终于释怀。不久,他病重去世,年仅三十六岁。太子陈伯宗继位,年仅十二岁,尊叔父陈顼为安成王,居于朝政核心。
从此,陈顼开始逐步削除异己。他先后设计诛杀掌握禁军的刘师知、到仲举,又除掉原属武将集团的韩子高——此人是陈文帝生前最亲近的将领,与皇帝私交甚笃,陈顼显然无法容忍他掌兵自重。
接着,陈顼将孔奂外放,稳住局势。公元568年,他正式废黜年幼的侄子陈伯宗,自立为帝,是为陈宣帝。
尽管登基过程饱受争议,但在位十年,陈宣帝政绩可圈可点。他重修水利,倡导节俭,缓解赋役,恢复农业生产,国内经济渐趋稳定。南陈也借此稍微摆脱了此前战乱的阴影。
公元573年,北齐政局崩乱,陈宣帝乘机北伐,派名将吴明彻出征,收复合肥等地,将淮南重新纳入南陈版图。这是南朝对北朝最后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军事反攻。
但好景不长,北周很快统一北方。公元577年,北周灭北齐,陈宣帝再次北伐,围困徐州吕梁。但此次北伐兵力分散、后援不足,吴明彻被围俘虏,南陈前期成果尽失,国力大耗。
之后的五年里,南陈国势每况愈下。北周则在战争洗礼中日益强盛,为未来的隋统一奠定基础。
公元582年,陈宣帝去世,年五十有余,传位长子陈叔宝。此人荒淫无度,不理政事,朝纲不振,八年后南陈亡于隋军之手。
发布于:广东省驰盈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